当唐诗韵律邂逅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文/《环球》杂志记者 刘娟娟
编辑/黄红华
当来自聂鲁达、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故乡的青年诗人们与从小受李白、杜甫、白居易熏陶的中国诗人们相聚在长安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在陕西和北京举行,来自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古巴等15个拉美国家的40位青年诗人与37位中国诗人齐聚一堂,以诗为纽带,展开了一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
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再到北海公园,从大学校园行到诗歌研讨会,中拉诗人们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增进了解、深化友谊,在诗歌的湍流中探寻人类文明的悠远回响。
诗歌无国界
“我从安第斯山脉走来,山川的秘密让我们亲如姐妹/爱意相交,双手紧握/山峰探到云里,都成了同一座/太阳要看到它,月亮要看到它/安第斯山脉与秦岭映照着同一片天空下的时光/中国,我愿用一生的脚步把你丈量……”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的中拉诗人深入秦岭腹地,用各自的语言共同为秦岭写了一首诗,尽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交流互鉴主题。
中拉诗人共同为秦岭写了一首诗(中国作家协会供图)
在陕西师范大学的诗歌朗诵交流会上,中外诗人们分别用母语朗诵自己的诗歌。“人类不过是/海洋中一间漂浮的小屋”“你不会毁掉这座桥/你会任它横跨河面/纵使河流已不复存在”“星光长满春日的枝头/宇宙早已入睡”……对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诗人们来说,朗诵诗歌的语言是陌生的,但读诗的声音、语调,以及朗读间隙短暂的停顿,无不让他们动容。
余音绕梁的吟诵表演《东篱酒影与花间月影》营造了古色古香的氛围,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在丝竹管弦的伴奏下吟诵了陶渊明、李白、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古巴诗人安东尼奥·赫拉达·希达戈说,这个表演让他认识了更多的中国古代诗人,“诗歌是人类交流的高级形式”,聆听中国诗人的诗歌,感受中国诗歌传统中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让他无比受益。
在西北大学的交流活动中,3位拉美诗人代表与3位中国诗人代表以及两位校园诗人代表,以“土地”为题现场进行即兴创作。“我们的地平线就像雪一样尘土升起,蜜蜂在大地上飞舞”“我的感情里面有土地的弧度,我的话语里面有土地的年轮”“太阳倾听万物,目睹万象,月亮感知洞察万千的梦”“土地是道路的总和,但也为我们提供偶尔的一脚踏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国度、不同语言,在那一刻,以“土地”为主题的诗歌组成一片诗歌的“土地”,涌动的情感汇聚成诗人们对世界与生命的理解。
智利诗人哈维尔·贝洛说,诗人是有国籍的,但诗歌无国界。“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柔软、最敏感的地方,就是诗意生发的地方。不同国家的诗人可以用语言把共通的意境、情感和思想传递给所有人。”
文明的回响
当墨西哥诗人阿德里安·门迭塔·莫克特苏马走进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兵马俑二号坑,看到镇馆之宝、目前唯一一座出土时完好无损的陶俑——它身着战甲,左腿曲蹲,右膝着地,双手置于身体右侧作握弓弩待发状——诗人无比陶醉。他找好角度拍下陶俑完整样貌后说:“兵马俑的庄严令人动容。这里的每尊陶俑都有独特的鼻梁曲线、迥异的面部形态以及个性化的手势。这些手势就像诗歌,不断传递着完整的情感。”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墨西哥诗人马努艾尔·夸乌特勒与“李白”在兵马俑前合影(中国作家协会供图)
步入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时光仿佛瞬间倒流回千年前的大唐街市。拉美诗人们一袭唐装,广袖轻扬,俨然成了穿行于盛世的异域旅人。他们用兑换而来的“银两”,在喧闹缤纷的商摊前驻足流连——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吃,欣赏皮影、折纸、折扇等各色工艺。萨尔瓦多作家劳里·克里斯蒂娜·加西亚·杜埃尼亚斯尤其沉醉于这些东方技艺。当她看到一位少女静坐莲池亭间,如画中之人,便主动上前合影,笑言“像是走进了某一句未曾写完的诗”。她说:“中国的唐诗与拉美的诗歌,向来不吝赞美自然。山川、流水、朝露,皆是我们创作中重要的元素。我们可以爱,可以思考,而诗歌正是这些爱与沉思的结晶,它让我们跨越语言,紧紧凝聚在一起。”
在西北大学的交流活动中,陕西诗人子非对于中拉文学中关于“时间”描述的观察颇为有趣,他说,从脚下的三秦热土延伸到拉美广袤的田野,两个文明产生碰撞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时间”,“在小镇阿拉卡塔卡马尔克斯童年生活的外祖母的庄园里,时间是缓慢的、绵长的;在三秦大地,农民一锄头挖下去就是两千年。”
中拉诗人们来到北京,在一个傍晚漫步慕田峪长城。夕照将整段长城点染成金色,远处是层层叠叠的松涛,近处烽火台的剪影让人迷醉。阿根廷诗人马克西米利亚诺·莱尼亚尼心中激荡着难以自抑的澎湃情感。他说,长城是他梦寐以求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今天梦想终于成真。在长城上,中外诗人们聊到博尔赫斯,正是这位被拉美、中国乃至全世界作家反复引述的文学巨匠,最早用中华文明的史诗意境与源远流长的神秘魅力,为阿根廷读者开启了认知的窗扉。“今日,我终于得以亲身体验这份传奇。”马克西米利亚诺·莱尼亚尼说道。
中国诗人马泽平说,博尔赫斯曾在其作品《长城与书》中探究过同一人或者事物不同的侧面,长城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拉美文学的一条纽带。在他看来,拉美诗人长于在作品中思考人类文明以及文化传承问题,而中国诗人更擅长小中见大,从琐细的生活细节中窥见事物本质,二者互相补充,和合统一,诗充当了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沟通的桥梁和媒介——正像此刻中外诗人们脚下的慕田峪长城,它在历史上曾作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物理分界,却在时间的风化中打磨成不同文明交融的苗床。
在西安永宁门,玻利维亚诗人杰西卡·弗罗伊登塔尔与一位“唐代仕女”合影(中国作家协会供图)
以诗歌为纽带,中拉友谊走向未来
智利诗人聂鲁达曾多次来到中国,并与诗人艾青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许多诗篇。参加“2025国际青春诗会”的智利诗人维多利亚·拉米雷斯·曼西莉亚也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20世纪初,她的曾祖父从广州漂洋过海到达智利北部海岸,与一位西班牙女性生育了13个子女,其中包括她的祖母。祖母虽不能流利地说中文,却记得一些儿时唱的中文歌曲。有一次,曼西莉亚的父亲下海游泳,在岸边的祖母忽然用粤语欢快地唱起童谣。那一刻,语言留下了无可辩驳的痕迹。曼西莉亚觉得,自己的创作灵感或许正源于祖母的童谣。这次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艾青书房,她想到了艾青与聂鲁达的交往。艾青曾在《在智利的海岬上》一诗中写道:“你爱海,我也爱海/我们永远航行在海上。”海,见证了两位诗人之间的友谊。
哥伦比亚诗人李戈自2006年起定居北京,如今已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在陕西师范大学的朗读交流会上,他朗读了自己用中文写的一首诗《圆形膝盖骨》:“我的祖先从那里下来/从时间凝固的海浪之巅/在蓝色地幔的远处/那被染色的巨大曲折/他们从那里下来。”
有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生问李戈,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中国与哥伦比亚在文化上有什么不同。李戈回答:“几万年前,美洲人的祖先从亚洲迁徙到美洲,而我如今从美洲的哥伦比亚来到中国北京居住。我在哥伦比亚是一名诗人,来到中国后也是一名诗人。诗歌是不会变的。经常有人问我:中国和哥伦比亚有什么不同?我更想回答的是两个国家之间有什么相同。在当下这个世界,我们更应该相互了解,拉近彼此的距离。”
来到中国后,秘鲁诗人尼尔顿·桑蒂亚哥想起了幼年时与父亲穿行于利马唐人街的情形。当年,那个男孩嘴里咬着一个包子,蹦蹦跳跳穿过拱门。现在因为这次诗会,这个长大了的男孩真的站在了中国大地上,邂逅了舞动的龙、泥塑的猴群等众多珍贵景象,以及大街上的喧闹和欢腾。他说,“诗歌以其强大的召唤力为我们提供支撑,将我们进行重塑。它搭建起桥梁,编织超越时空的纽带。”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短短几天的行程中,中国与拉美诗人们或围坐畅谈诗歌创作中的感想,或俯身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思想的碰撞与观点的交融从未停歇,也让彼此之间的心灵贴得更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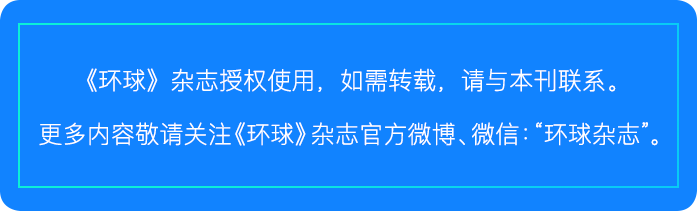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