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独居现象调查
 在德国首都柏林,人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户外区域
在德国首都柏林,人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户外区域
文/《环球》杂志记者王自强(发自柏林)
编辑/胡艳芬
在柏林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清晨,街角的面包店里,许多顾客都是独自前来,买好早餐便匆匆离开,踏上通勤的轻轨。这样的生活场景,在德国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上演——一个人生活,不再是极个别人的选择,而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日常。最新统计显示,独居群体已成为德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
独居人口显著增长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4年,德国约有1700万人独居,占总人口的20.6%,相当于每5个人中至少有1个人独居,这一比例较2004年的17%增长了3.6个百分点;过去20年间,德国独居人口总数增长了21%,从2004年的1400万人增加至1700万人。
实际上,这一趋势并非德国独有,而是整个欧洲的普遍现象。
2013年至2023年间,几乎所有欧盟国家的独居人口比例均有所上升。欧盟平均独居人口比例从2013年的14.2%上升至2023年的16.1%。其中,保加利亚增幅最大,从8.5%上升至17.8%,增幅达9.3个百分点;其次是立陶宛,从16.1%上升至24.6%;芬兰从19.6%增至25.8%。相比之下,德国的独居人口比例虽然增幅不大,但始终保持在20%左右,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仅次于北欧等高独居率国家。
从年龄结构看,德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中,34.6%的人选择独居,显著高于欧盟31.6%的平均水平;85岁以上高龄人群的独居比例更是高达56%;25岁至34岁的年轻人群体中,独居人口占比也达到28%,高于全年龄段平均值。可以说,独居已不仅仅是老年人群的特征,也越来越成为青年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这种居住结构的转变已成为德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家亚历山大·兰根坎普指出,这一趋势并非近几年才出现,而是德国统一前就在原联邦州存在,在统一后持续加强。
 在德国柏林,行人在阴凉处躲避日晒
在德国柏林,行人在阴凉处躲避日晒
流动性、个性化与社会变迁
为何选择独居的德国人不断增多?兰根坎普指出,这是多种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
首先,人口老龄化是原因之一。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医疗条件改善,一些老年人在失去配偶后仍能长时间独立生活。此外,部分老年人尽管仍有伴侣,也可能因为健康状况、护理需求或生活理念的不同而选择分居或单独生活。
其次,职业选择与流动性加剧导致独居生活成为部分人的现实选择。许多德国年轻人为了教育或就业迁移到其他城市或国家,从而远离原先的家庭。在新城市,不少人选择更具灵活性与自由度的单身生活。
此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独立促使独居现象更加普遍。尤其是德国女性群体,过去常因经济依赖而选择与伴侣同居,而现在凭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能力,更有条件作出自主选择。更多的女性在职业生涯发展期选择独居,以实现个人成长和拥有空间自由。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推动了德国的社会规范和生活理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们更加追求个性化,社会也越来越能够接受并尊重个人选择,单身、分居、异地伴侣等生活方式不再被视为异类,而成为多元社会中的常态。一些人有伴侣也仍然选择独居生活,这种现象更加普遍,尤其是在城市中。
最后,还存在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在现实中放大了人们之间的心理隔阂。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等帮助人们更加便捷地保持联络,却无法完全取代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且使这种互动减少。瑞士《新苏黎世报》指出,在生育率降低、家庭规模变小的背景下,代际之间关系变得更为冷漠,祖孙之间的接触日益减少。德国波鸿大学心理学家迈可·卢曼主持的研究表明,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新冠疫情期间的数字依赖显著增强了他们的孤独感与社交疏离。
建立关怀机制
尽管独居是一种个人选择,但其社会后果不容小觑。数据显示,独居人群面临更高的贫困和健康风险。2024年关于德国国民收入和生活状况的调查显示,独居者中约有29%面临贫困风险,是普通人群15.5%的近两倍。老年人群尤为脆弱,一旦失去收入来源或患病,就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德国下萨克森州贫困问题会议执行主任法比安·施滕肯指出:“这种发展态势也体现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贫困人口更有可能独自生活,并被系统性地排斥在外。”不仅老年人,城市里的年轻独居者也存在经济和情感支持缺失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德国联邦政府于2023年12月通过了首个国家级《对抗孤独战略》,这标志着政府开始从政策层面系统性应对这一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联邦家庭事务部长莉萨·保斯在发布会上指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对社会失去信任而退缩,这不仅削弱社会凝聚力,更将对制度构成威胁。”
该战略计划包括如下几项措施:举办“反孤独行动周”,通过宣传和媒体引导,提升社会公众对孤独问题的认识;鼓励各类企业、公共服务机构开展员工培训,增强识别并干预孤独现象的能力;为孤立人群提供更多休闲与社交活动资源,例如读书会、运动团体、社区互助小组等;加快心理健康支持服务的响应速度,尤其是关注精神疾病与社交障碍患者的早期介入。
然而,该战略仍面临执行层面的现实障碍。德国患者保护基金会批评政府没有提供额外的财政预算,而是将任务交由地方组织和现有机构承担。这些组织常常由于人力不足、资金紧张等原因,难以开展系统化的干预项目。此外,目前孤独问题在立法体系中的地位尚未明确,相关行动缺乏法律保障与强制执行力。从长远来看,如何在尊重个体自由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联系、重构互助网络,仍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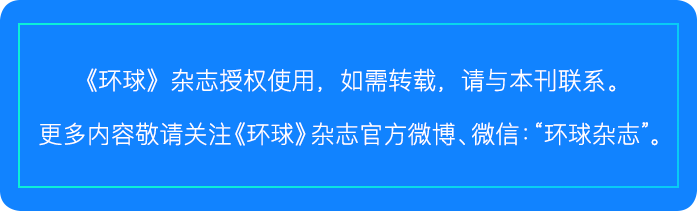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