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东藏
文/桂涛
编辑/胡艳芬
我和藏书人刘铮约在广州一座高楼上的一间咖啡馆见面。落地窗外,珠江蜿蜒流淌,我们的脚下是曾向西方“一口通商”的十三行遗址,远处是三元里抗英纪念碑。在这座始终处于中西对话前沿的城市,讨论刘铮的《西书东藏:中国文化名家的外文藏书》(以下简称《西书东藏》)再合适不过。
这本书在中国人的藏书史研究上堪称“前所未有”。它写的是梁漱溟、周作人、萧乾、钱锺书等中国37位现代学者、作家、文化人曾读过、收藏过的外文书。刘铮通过研究这些知识分子散佚久矣的藏书,揭开了笼罩他们精神世界的幕布一角,也让人对西学东渐、东西文化汇流有了新的思考。
曾经,他们搜求它们、阅读它们,而它们滋润他们、丰盈他们。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藏书颠沛流离,在刘铮的书房里重聚,让那些消散在时光里的思想对话再度苏醒。
刘铮像个侦探,他通过探究书上留下的签名、钤印、批注、折页等“书之痕”,重构还原当年人与书之间的关系,窥探那个时代的知识版图。通过一次次“知识考掘”,他要唤醒那些隐没在典雅丰赡的外文旧书中的中国灵魂和猜度其中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
比如,刘铮曾买到一本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的《杂俎五集》,此书是著名翻译家赵萝蕤(ruí)的旧藏。在赵的回忆文章和别人回忆赵的文章中,都提到她曾在法文课上读过瓦莱里的作品,有人甚至据此断定,她的作品深受瓦莱里的影响。刘铮发现,那本需要边裁边读的《杂俎五集》毛边本只有第一页被裁开,因此断定赵并未认真阅读过这本书。
再如,他发现历史学家周一良当年在哈佛大学读过的一本厚厚的语言学著作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页面上都有周的划线和批注,而这本书在《周一良全集》中竟然毫无痕迹。刘铮因此推断,周一良一生中可能对不少书都下过同样大的功夫,确是扎实治史。
虽然这样的发现对普通读者可能没什么意义,但刘铮认为,将这些隐藏的细微历史挖掘和讲述出来,能“让历史的颗粒度更加清晰”。
真正的阅读史,或许就存在于那些从未裁开的书页与密密麻麻的批注的张力中。一枚藏书票可能是文化迁徙的签证,一道铅笔划线或许暗藏思想的交锋。
我认为,《西书东藏》的贡献之一是,它为藏书人带来了关于藏书的更多思考角度:
比如,那些外文书被中国文人们从世界各地买来,又带到世界各地阅读,日内瓦、维也纳、东京——单是这些购买地和阅读地就展开了一种书籍文化的“拓扑结构”(编者注:一种强调关系和连通性的结构)、一份全球知识流动的地形图和微观史。
这些留有历史痕迹的外文书对收藏者提出了识伪辨伪的要求,比如签名、印章、题签等是新是旧。刘铮认为,书斋里的生活就是坐在扶手椅上,而辨伪的过程则像是扮演一次侦探。
刘铮坦承,和那些一掷千金的藏家相比,他所藏的这些“西书”可能只是小儿科,但他仍“敝帚自珍”。毕竟西谚有云:“我的杯子虽小,但我用自己的杯子喝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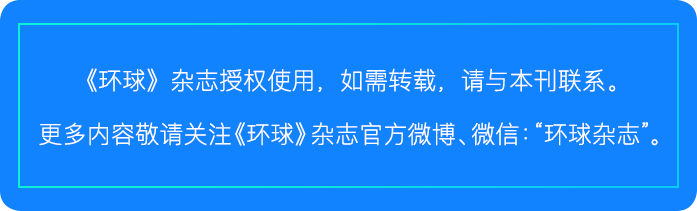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
